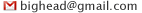今夜,我们用双脚丈量深圳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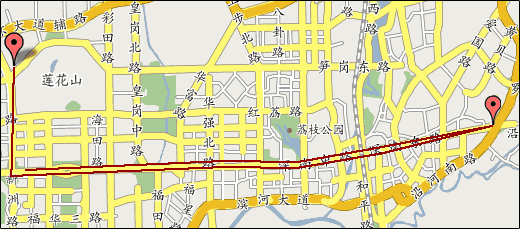
在收到靳老师的短信之前,这本来应该是一个百无聊赖的夜晚。“去不去暴走?”读完只有五个字的短信,我的心中啪的一声,像是折断了一根筷子。
这个夜晚有救了。
暴走深圳这件事,其实只是我和靳老师一周前无意间说起的愿望。我们的想法是找一个没有睡意的夜晚,像野鬼一样去这个城市里行走游荡,无所谓终点,也不在乎方向。然而所谓光阴似箭,真的一点也不错,因为才一转眼我们便已经站在了北大医院门前。这是三月三日,夜里十点三十分。
出于对深圳治安的不信任,我只在身上放了些钱,还有手电和地图。本打算揣上那柄从新疆带回来的英吉沙刀,想起胡家刀法已经生疏很久,只好作罢。靳老师则更加彻底,除了家门钥匙什么也没带,两手往衣兜里一插,就屁颠颠跟我上了路。
 像大多数饱食终日的人们一样,长期以来我与先锋(或曰实验、前卫)艺术并不曾发生过太多的关系。我从不会因为无法理解他们而自惭形秽,但也不会恼羞成怒地认定他们都是垃圾。有些时候,我甚至还很乐意跟昨天夜里一样,花几个小时接近他们,试图了解他们那个世界的样子。
像大多数饱食终日的人们一样,长期以来我与先锋(或曰实验、前卫)艺术并不曾发生过太多的关系。我从不会因为无法理解他们而自惭形秽,但也不会恼羞成怒地认定他们都是垃圾。有些时候,我甚至还很乐意跟昨天夜里一样,花几个小时接近他们,试图了解他们那个世界的样子。 我的老家是一个只有五六百人的小山村。二十几年来,那里一直宁静无比,并没曾发生太多的变化。但是我知道,它迟早要和整个世界一样,成为我不认识的模样。因此,在这件事发生之前,我想为它做一些简单的记录,尽管我还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更多的意义。
我的老家是一个只有五六百人的小山村。二十几年来,那里一直宁静无比,并没曾发生太多的变化。但是我知道,它迟早要和整个世界一样,成为我不认识的模样。因此,在这件事发生之前,我想为它做一些简单的记录,尽管我还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更多的意义。 你过年回家吗什么时候回去啊火车票买好了么,是这个时候深圳最泛滥的话题。
你过年回家吗什么时候回去啊火车票买好了么,是这个时候深圳最泛滥的话题。 1901年11月,李鸿章老师去世。据说,李老师死前曾如是力荐直隶总督人选:“环顾宇内,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。”奇怪的是,袁世凯此等大枭雄,自民国有史以来却并无一本对其有正面评价的书。治史家们是不为也,或不能也?
1901年11月,李鸿章老师去世。据说,李老师死前曾如是力荐直隶总督人选:“环顾宇内,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。”奇怪的是,袁世凯此等大枭雄,自民国有史以来却并无一本对其有正面评价的书。治史家们是不为也,或不能也? 从前为了附庸风雅,找过一些张静娴的唱段来听。初开始完全听不明白唱的什么,耳中只有鸡鸭鱼肉四个字。“袅晴丝吹来闲庭院”,八个字便用了四十几秒才唱罢,那样缠绵婉转,柔柔慢慢,叫我很是替歌者着急,极想用力帮她把声音从嗓子里拉出来。但是看了歌词,立刻明白自己的急性子有多可笑。那样的词,真是要配了那样的水磨调才最合衬——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,赏心乐事谁家院。
从前为了附庸风雅,找过一些张静娴的唱段来听。初开始完全听不明白唱的什么,耳中只有鸡鸭鱼肉四个字。“袅晴丝吹来闲庭院”,八个字便用了四十几秒才唱罢,那样缠绵婉转,柔柔慢慢,叫我很是替歌者着急,极想用力帮她把声音从嗓子里拉出来。但是看了歌词,立刻明白自己的急性子有多可笑。那样的词,真是要配了那样的水磨调才最合衬——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,赏心乐事谁家院。![Happy new year 2006,新年快乐!
[ image by Juque.cl ]](http://www.bighead.cn/uploadimg/happy_new_year_2006.gif) 应该没有太多人会厌恶新的一天吧,特别是,当它恰好还是新一年的第一天时。无论之前如何艰难或者顺遂,新的一天和一年,总能给人们一些一厢情愿的期待,祈祷厄运远离,希望幸福常在——尽管我们早已知道,该来的总会来,该走的也留不住,“未来他一直来一直来,不管好或坏”。
应该没有太多人会厌恶新的一天吧,特别是,当它恰好还是新一年的第一天时。无论之前如何艰难或者顺遂,新的一天和一年,总能给人们一些一厢情愿的期待,祈祷厄运远离,希望幸福常在——尽管我们早已知道,该来的总会来,该走的也留不住,“未来他一直来一直来,不管好或坏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