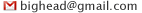我们不是那么幸运的人
一些人发足狂奔、怒抱彼此,另一些人委顿在地、长跪不起。天堂地狱之间,伊斯坦布尔的夜空仍旧星月低垂,博斯普鲁斯海峡难见一点波澜。毕竟,几万人的悲欢竟可以呈现如此强烈而残忍的反差,自拜占庭以降的数千年里,它们早已见证太多太多。
我们终究不是那么幸运的人啊。十三年来陪伴这只球队遍历光明与黑暗,凌晨三点相聚各个城市的酒肆红眼督战,不远万里奔赴现场群情激昂,在巴士里在酒店前在看台上在几乎所有地方为他们嘶声高唱——这些当然不容易,但正如人生一样,许多时候并不是做到了什么,期望的结果就一定能随之而至。世界从来不会给出这样的承诺,这一次,我们也没有那么幸运。
然而我们却又如此幸运。十三年后球队得以再飨欧冠荣光,本身已是远超预期的巨大惊喜。而在许多人以为我们将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这一夜,球队令人骄傲地战斗到了最后一刻,昂首离开球场。得以在伊斯坦布尔亲见这一切,我们,何其幸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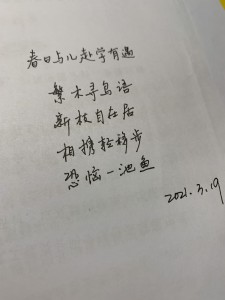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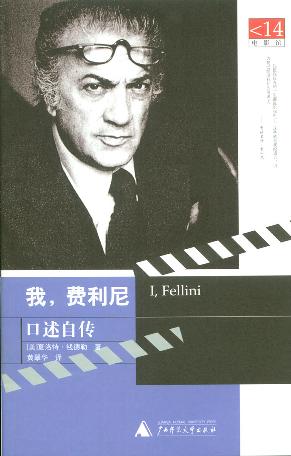 「独处是一种特别的能力,有这种能力的人并不多见。我向来羡慕那些拥有内在资源、可以享受独处的人,因为独处会给你一个独立空间、一份自由,这些是人们嘴上喊『要』,实际上却害怕的东西。……他们害怕寂静无声,害怕那种剩下自己一人,与自我思绪及长篇内心独白独处的静默。因此,你必须很喜欢和自己做伴。好处是,你不必为了顺从或讨好别人而扭曲自己。」
「独处是一种特别的能力,有这种能力的人并不多见。我向来羡慕那些拥有内在资源、可以享受独处的人,因为独处会给你一个独立空间、一份自由,这些是人们嘴上喊『要』,实际上却害怕的东西。……他们害怕寂静无声,害怕那种剩下自己一人,与自我思绪及长篇内心独白独处的静默。因此,你必须很喜欢和自己做伴。好处是,你不必为了顺从或讨好别人而扭曲自己。」  中国的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。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。农民离家去城里找工作是怎么一回事?教人们怎么做生意的是谁?他们在哪儿学到汽车制造技术的?他们是如何琢磨出怎样开车的?谁教会小镇上那些精明的女人穿衣化妆的窍门?什么时候开始,推动这个时代的已经不是大规模的政治事件和强力领袖,而是走向城市的农民和边学边干的企业家?
中国的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。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。农民离家去城里找工作是怎么一回事?教人们怎么做生意的是谁?他们在哪儿学到汽车制造技术的?他们是如何琢磨出怎样开车的?谁教会小镇上那些精明的女人穿衣化妆的窍门?什么时候开始,推动这个时代的已经不是大规模的政治事件和强力领袖,而是走向城市的农民和边学边干的企业家?